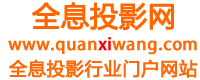在俞潔的作品里蒙著臉的人,人物用來表達(dá)的嘴、用來聆聽的耳朵都被遮住,只剩下一雙眼睛。事實(shí)上在一個急速變化的國度,所有經(jīng)驗(yàn)判斷常會使人蒙羞,而當(dāng)代生活仿佛是一部全息影像。同時,這些形象去掉了表情,被遮住的不只是臉,而是臉的社會性,俞潔因此讓人的面容變得更干凈,變得不再那么重要,從而也成了對臉部表情的意識形態(tài)的一種反駁。
在這里,“面具”就像帷幔,后面永遠(yuǎn)停留著好奇,永遠(yuǎn)有另一種存在。面具也是禁忌、是界限,同時也是某種庇護(hù)。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說:“人類失去了一個形象,一個無法重新見到的形象。”而讓我們感到的是在“易容”和“隱身”盛行的當(dāng)代,人的面容已漸漸模糊。說到底,所有被記住的面容,都是面容之外的光芒,而非其本身。
俞潔新近的繪畫,放棄了前些年那些帶有涂鴉意味式的即興方式,更多了“寫”的成分,作為一個強(qiáng)調(diào)東方性的藝術(shù)家,她以溫和的形式將現(xiàn)實(shí)性隱匿到形象背后。
她制造了很多看起來過于干凈的畫面,人物形象都有自足性,這些人和物都沉浸在自己的專注中,而不與看作品的人對視,也就是說沒有發(fā)現(xiàn)“被看”。那么他們在做什么呢?例如,有人在洗馬——卻是匹木馬;有人在粒子里祈禱——是爆炸的粒子等。細(xì)辨之下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他們都是在干著非日常的事情,更像是一種姿態(tài)和表演。
如同在儀式中一樣,在畫面上制造的氣場,也能讓日常之物脫離了它的屬性,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,同樣,作為一個習(xí)慣于沉寂的藝術(shù)家,通過繪畫本身在內(nèi)心獲得“圣潔”,她用畫筆讓自己稍稍飛離地面,飛離喧囂的現(xiàn)實(shí)。在一定程度上畫什么其實(shí)不重要,重要的是畫畫的姿態(tài)應(yīng)該是清晰可辨的,重要的是畫布后面的那個形象。